歷史的偶然與必然-- 金庸一生中交織著的偶然與必然
以創作新派武俠小說而知名中外的香港作家金庸(本名查良鏞),於2018年10月30日下午在香港養和醫院含笑辭世,親友在旁,積壽94年。
內地網媒相關的報道、社交媒體上的議論,隨即鋪天蓋地而來,內地都市報亦以罕見的六至十個版位的篇幅,講述金庸筆下的江湖,其亢奮的狀態遠遠超過香港的報章。金庸喪禮按生前意願以私人方式舉行,中央集體領導人送來花圈,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,總理李克強等等…新華社的新聞稿稱,金庸在香港回歸的過程中作出了貢獻。新華社所指的,當是金庸以報人身份的活動,而非武俠小說家的身份。
金庸曾說:「《明報》是我的畢生事業與聲譽」,對廣大的內地讀者來說,很多人還不知道金庸大俠就是香港《明報》的創辦人,更不知道金庸開筆寫武俠小說是在玩票的情況下進行。歷史的發展,雖然有必然性,卻往往帶有偶然性;金庸的一生,交織著「必然」與「偶然」。
金庸是浙江海寧縣人,生於1924年,金庸的童年與青少年期,是在抗日戰爭中渡過的。1937年「七七」事變後,戰火波及浙江,金庸隨著嘉興中學師生徒步遷入西部山區上課,過著漂泊流徙的生活。戰爭把金庸訓練得很大膽,他唸高中及大學時,曾接受軍事訓練,會開槍、擲手榴彈。抗戰時曾踏自行車走千里路,從浙江到重慶唸大學,途中日軍炸彈就在車旁炸開了一個大洞。流徙的生涯,強化了金庸的民族感,也豐富了金庸的見聞和文學修養。他曾在西南窮鄉僻壤生活了兩年,那是苗人漢人聚居之地,人人都是天生的歌手。冬日晚上,漢人苗人圍著火堆,邊烤紅薯邊唱歌。金庸就用鉛筆一首首地記下來,記了三大冊共一千餘首。中國民歌這種富有民族特色的文體,豐富了金庸的文采,在他日後撰寫小說和撰寫政論文章方面,都能用得上。金庸分析自己所寫的《書劍恩仇錄》能夠受到不同文化水平的讀者歡迎,正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原因。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,金庸考入杭州《東南日報》做記者。1947年,金庸考入上海《大公報》,1948年被報社派去香港,參加香港版的籌辦工作,在香港《大公報》前後工作了十年,由此便與香港報業結下不解之緣。
據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的上司副總編輯羅孚(本名羅承勛)的兒子羅海雷撰寫的「查良鏞與《大公報》的小秘密」一文披露,當年老闆胡政之從天津、上海、重慶三館調派二十人到香港,名單上並沒有金庸。羅海雷說:「名單裏面的一位上海同事,當時剛剛新婚燕爾,不願勞燕分飛,這個苦差事只好讓查良镛代勞。」
金庸筆下的江湖人物,往往有許多奇緣,一個偶然的因素,就改寫了一生的發展。金庸本人也可如是看,金庸到香港是命運的一大轉折,這一轉折,原來也是出於一個偶然。
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,當時香港《大公報》可以內銷大陸,但是一如其他的內地報紙,報道朝鮮戰事受到嚴格限制;《大公報》為了及時報道戰爭消息,爭取香港讀者,於是籌辦另一份政治旗幟並不鮮明的《新晚報》。同年金庸辭職北上外交部求職,基於家族及無党派背景,無法叩開外交部的大門。金庸外交官夢碎後回港企圖重返《大公報》,卻受到報社部份員工的阻撓,報社領導愛材,把金庸調去了《新晚報》,這才有了參與撰寫武俠小說的契機。現在回頭看,這一連串的機緣巧合,隱隱然為金庸打開了一條方向。
新派武俠小說的源起,坊間各有說法。最早最權威的說法,見諸當事人梁羽生1956年9月7日在《新晚報》的一篇文章。梁羽生本名陳文統,是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的同事,面對著面辦公,工作之餘經常在口頭上比劃詩詞武功,大談招式人物。梁羽生憶述:「…吳、陳拳賽之後(筆者按:即1954年1月17日下午四時,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,5千香港人前往觀戰,比賽只打了幾分鐘,以吳公儀一掌打得陳克夫鼻子流血而終止。),我和金庸、百劍堂主(筆者按:百劍堂主即《大公報》副總編輯陳凡)三人同在一室工作,《新晚報》的總編輯羅孚兄是我們很熟的朋友,有一天(筆者按:應是比賽後第二天)他匆匆跑來,說道,我要一段武俠小說,後天交稿,你們必定要替我想辦法﹗我們三人,誰都沒有寫過武俠小說,但不寫又不行,後來我們開玩笑的成立一個協定,每個人都要替《新晚報》寫一部。三人中百劍堂主是老大哥,金庸兄比我大一歲,算是二師兄,按武俠小說的規矩,薑是老的辣,最老的那位總要到最後才出場,於是便排定了登場之序,由我打第一炮,接著是金庸,百劍堂主則橫劍鎮住陣腳。」三天後即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的《龍虎鬥京華》在《新晚報》見刊。梁羽生這一番說話過於謙遜,內容不盡可信,但至少也反映出三人起初對寫武俠小說,是抱著玩票不恭的態度,沒有想到日後作品可以登上文學殿堂。事實上,五十年代香港以大報自居的報紙,不會刊登武俠小說,認為不入流、不夠格;內地則以寫實文學為主,更沒有武俠小說的生存空間。
梁羽生以其對歷史詩詞的學養,以義和團為背景、以寫意手法寫出了武打的《龍虎鬥京華》,聲名立時大噪,報紙只要刊登梁羽生小說,必然有銷量,一改香港報章對武俠小說的態度。
1955年2月8日,《新晚報》在第一版刊登啟事:「……今天起增加兩個新的連載:其一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……。」《書劍恩仇錄》第一集在1955年2月8日《新晚報》刊登。金庸在1955年10月5日《新晚報》「漫談書劍恩仇錄」中這樣回憶他開始以金庸為筆名寫武俠小說的緣起﹕「八個月之前,《新晚報》總編輯和『天方夜譚』的老編忽然向我緊急拉稿,說《草莽》已完,必須有『武俠』一篇頂上。梁羽生此時正在北方,說與他的同門師兄『中宵看劍樓主』在切磋武藝,所以寫稿之責,非落在我的頭上不可。可是我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啊,甚至任何小說也沒有寫過,所以遲遲不敢答應。但兩位老編都是老友,套用《書劍》中一個比喻,那簡直是韋駝子和文四哥之間的交情,好吧,大丈夫說寫就寫,最多寫得不好挨罵,還能要了我的命麼﹖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報館,說小說名叫《書劍恩仇錄》。至於故事和人物呢﹖自己心裏一點也不知道。老編很是辣手,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裏來,說九點鐘之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,否則明天報上有一大塊空白,就請這位工友坐著等我寫。那有什麼辦法呢﹖於是第一天我描寫一個老頭子在塞外古道上大發感慨,這個開頭下面接什麼全成,反正總得把那位工友請出家門去。」
《書劍恩仇錄》報紙上的第一篇就是這樣開始的﹕
第一回﹕「塞外古道上的奇遇」。篇首道﹕「『將軍百戰身名裂,回頭萬里,故人長絕。易泣蕭蕭西風冷,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,料不啼清淚啼血。誰共我,醉明月。』這首氣宇軒昂、志行磊落的《賀新郎》詞,是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的作品。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,騎在馬上,滿懷感慨地低低哼著這首詞。這老者年近六十,鬚眉皆白……。」這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,在現實的生活當中,就是坐在金庸門外賴著不走催稿的老工友﹗
金庸性格好勝,眼看梁羽生短短一年便名利雙收,自是手癢難耐,恰好有了梁羽生竭息停產的機會,即不失時機的站到了幕前。雖然梁羽生珠玉在前,亦掩蓋不了金庸的鋒芒,一時梁金並稱,馳騁江湖。
金庸在開展辦報生涯前,曾經刻意追求兩個事業而無功,一是他的外交官夢,一是他的導演夢。
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的十年,同期編寫電影劇本。1953年,金庸以林歡為筆名,為長城電影公司編寫《絕代佳人》劇本,並且獲中國文化部評選為1949-1955年期間的優秀影片。從1953年至1958年,當金庸的名字還是不大為香港人熟悉的時候,林歡一名,在香港國語片電影圈中,則是赫赫有名。1957年金庸離開《大公報》,全職在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劇兼導演,同時也繼續為《新晚報》寫武俠小說《雪山飛狐》。長城公司總經理袁仰安對金庸頗為器重,經常把《長城畫報》的顯著篇幅,刊登金庸的電影評論文章。在這段時期中,金庸幾乎已成為香港左派電影的理論家。隨著內地三反、五反政治運動,也慢慢波及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。金庸的電影理論基礎是西方的,自然受到左派電影公司中的左傾同事的批鬥,金庸刻意要在電影圈闖出一番事業,也變成不可能了。
常說命運關了一扇門,同時也會為你打開另一扇門。金庸在苦無出路之際,1958年他為《香港商報》撰寫的《射鵰英雄傳》,卻取得意外的空前成功。《射鵰》的故事發展,成為香港街談巷議的話題。泰國曼谷的中文報紙,為了搶先轉載《射鵰英雄傳》的內容,不惜以電報來轉發。南洋、美洲各地的僑報,也紛紛轉載梁羽生、金庸的武俠小說。
1958年,香港盜版翻印武俠小說的情況非常普遍。金庸每天寫一千字,由於當時沒有版權的意識和法例的保護,金庸小說每七天就被人結集盜印成單行本出版。當時金庸的老同學沈寶新在嘉華印刷廠當經理,沈寶新建議,與其被別人盜印成小冊子發行,不如自己印,自己發行,自己賺錢。加上《香港商報》的調查顯示,金庸讀者至少有三萬人,自行出版,大可封了蝕本之門。有了這個意圖,金庸與沈寶新匆匆忙忙的著手開始籌辦十日刊的《野馬》武俠小說雜誌了。 在籌備期間,報販發行們建議與其出版十日刊期刊,不如出版日報,理由是日報天天出版,現金回籠更快。於是金庸沈寶新二人馬上轉而籌備日報。金庸1955年以玩票態度寫武俠小說,想不到積累下來的讀者群,讓他可以在香港小報叢生的局面下,辦起了一份武俠小報,為自己的命運翻開新的一頁。金庸走上辦路之路,看似「偶然」,也處處有「必然」的成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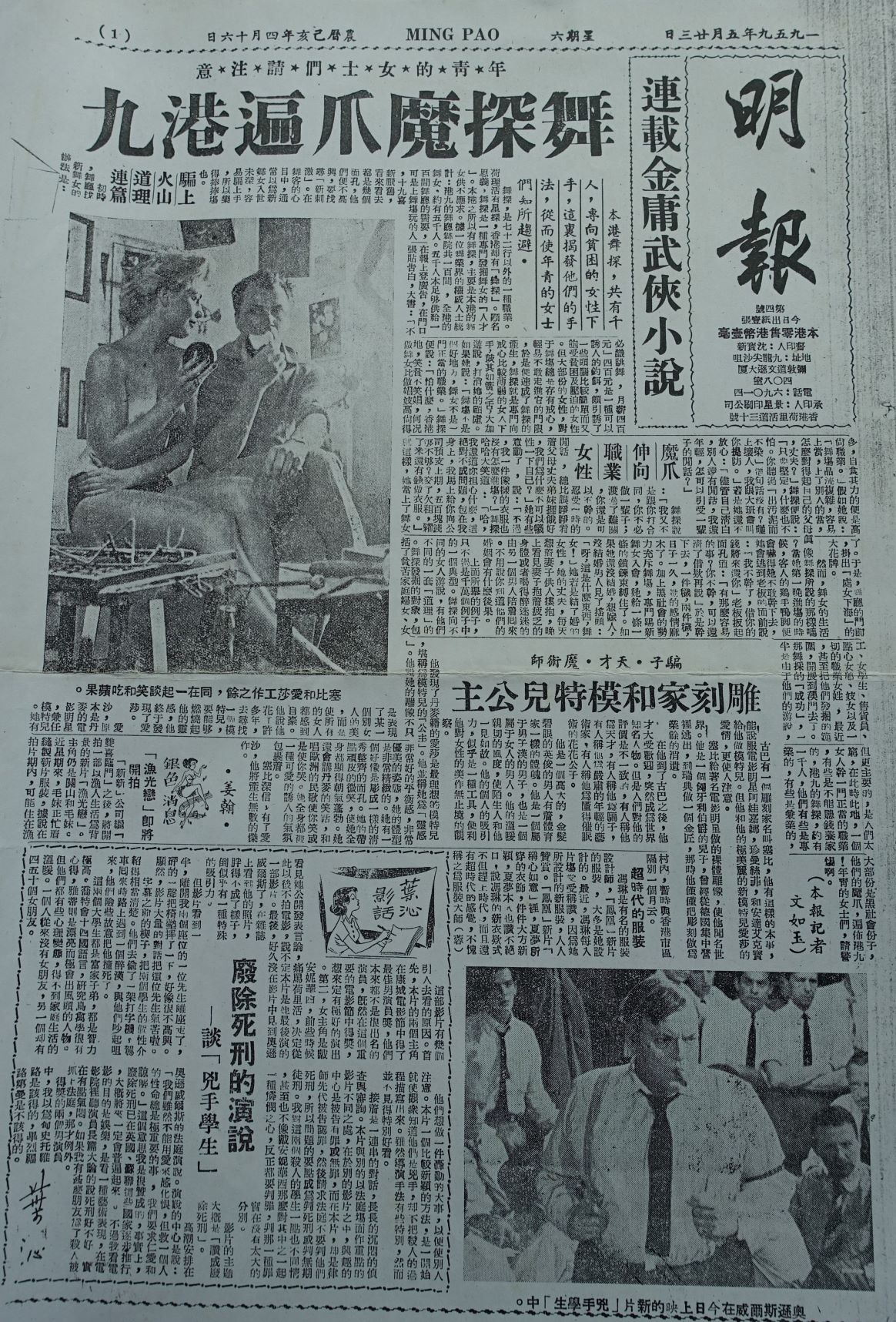
金庸1959年5月20 日創辦《明報》,辦報初心,只是想改善經濟收入,因此初創時期,不談政治,不講高尚人生,以小市民為讀者對象,篇幅上盡是好來塢的電影明星裸照、罪案色情新聞,副刊以金庸武俠小說為號召,也有誨淫誨盜的文章、狗經馬經並存。
在報章寫連載武俠小說,每天一千字,一年要寫三百六十二天,只有農曆新年可以休息三天,也是很苦的差事。1959年9月27日, 金庸所寫的《神雕俠侶》,在小說版消失了。編者解釋作者有病,暫停一天。到了9 月28日,《神雕俠侶》仍未見刊,編者說「金庸先生不適,讀者函電紛馳,小說明天見報,神雕迷請釋念。」金庸迷一齊起哄,金庸只得抱病爬格子。
金庸的武俠小說,凝聚了金庸迷的共同心願,在小說連載期間,讀者時有去信金庸,主動就情節的發展提供意見,金庸也很善於吸收意見,再運用本身豐富的學識和文學修養,寫出了廣受歡迎的成年人童話。沒有報紙連載的壓力,金庸文學造詣再高,也不可能有這麼高的產量;沒有金庸的學養和識見,有了一個報紙框框,充其量也只是眾多報紙專欄作者之一而己。
金庸辦《明報》,把1959年的一份小報發展成為1980年代一份知識份子喜愛閱讀的大報,每一個階段的發展,都與國內外政局發展息息相關。金庸曾把《明報》的發展,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:一是1962年內地人大量湧入香港的浪潮,一是1966年至1978年為期12年的文化大革命。金庸辦報的首三年費盡心力,銷量一直在二萬份左右,沒有突破,1962年內地人大量湧入香港,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。新增加的人口,雖然來了香港,還是很關心內地的發展,《明報》員工很著力的報道內地消息,報紙銷量大增,金庸也默許這種改變。
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,金庸逐步減少《明報》的小報內容,增加了「文革」的獨家新聞,加上金庸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,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,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。如何具體引起外國政府對《明報》的關注,這裡補上一筆:1982年筆者以《明報晚報》採訪主任的職位採訪中英香港前途會談,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英國外交官口中得知,《明報》報社內有一名高級職員收受國民党特務機構的津貼,我馬上把這個訊息面告金庸,金庸即時的反應是:那也太小看《明報》了,我們豈止有國民党的特務,報社內還有美國CIA特務、蘇聯KGB的、英國MI6的…金庸把員工名字也一起數算出來,我大受震驚,問金庸:「為什麼不把他們辭退?」金庸說,他們留在報社不好嗎?我們有什麼動向,各國政府馬上知道,不用以訛傳訛。《明報》日後有了英譯社評,公開上說是推動英語學習,最初的考量卻是滿足各國駐港領事館的需求。在香港經營傳媒的複雜性,由此可見一斑。
《明報》1963年的銷量是5萬份,「文革」開始後升至10萬份,1989年躍升至超過20萬份。每每在內地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,《明報》銷量都有飛躍式的增長。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15部武俠小說《鹿鼎記》後宣布封筆,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份,活躍在海峽兩岸。 1973年,台灣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接見金庸;1981年,鄧小平接見金庸;1984年,胡耀邦見金庸;1993年江澤民接見金庸。香港以至海外報人當中﹐如此頻密地獲得海峽兩岸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例子並不多見,足以反映出《明報》的影響力。
兩岸領導人接見金庸,與金庸的國事取態有關,1973年6月7日,金庸訪問台灣返港後一連十八天在《明報》刊登「在台所見、所聞、所思」,在這系列文章中,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,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,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。
隨着北京糾正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做法,在七十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,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,1972年與日本建交,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。這些事態的發展,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。《明報》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,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,持肯定的態度,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,多了點溫情,多了點中國文化。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人,態度更轉趨溫和。香港的左派及右派因此長期攻擊金庸,說他是風派、牆頭草。1982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外交談判,期間英國不斷拋出各種方案,又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,強化香港人在管治上的角色,希望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。金庸當時是港督府的常客,也經常接見訪問香港的英國國會議員,在言論上多少亦受到英國的影響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與鄧小平見面後訪問香港,單獨與金庸會面,要求金庸支持英國在談判上的立場。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,金庸一口拒絕了戴卓爾夫人的要求,堅決支持香港在九七年後整體回歸中國。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,金庸以極大的熱情,投入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。金庸一向公開認為,管治香港的不二法門是:自由+法治=繁榮+穩定。這個方程式並不需要民主的存在。金庸在這個思路下制定的香港政制發展路線圖,被右派及香港部份民主党派批評為忽略民主訴求、保守左傾,數名大學生甚至在報社門前火燒《明報》,金庸對此耿耿於懷。金庸本意以武林盟主身份主持政制討論,擺平各派意見,現實卻是各派並不賣帳,在這個困境下,加上八九年春夏之交內地發生的一場政治風波,金庸順勢辭去基本法草委工作,也著手部署從報界引退。1991年《明報》報業集團上市,以每股2.9港元發行面值0.1港元的新股7500萬股,淨得資金2億港元。金庸沈寶新以10萬港元創辦《明報》,經過32年的經營,實現資產估值近6億港元。金庸以一支筆,創造出數億元的財富,不能不說是當代報業的一個奇蹟。《明報》上市前後,不少海外投資者提出收購,美國報人梅鐸提出以十億港元收購《明報》,條件是要金庸為梅鐸打工三年,金庸不想為梅鐸打工,更不想《明報》落入外國人手上。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後,金庸主動引入並借出股票協助智才集團的于品海收購《明報》,自己選擇退居幕後,以「太上皇」的身份,繼續掌控編輯方針。《明報》在于品海經營下,股價由長期停滯不前的二元價位攀升上十元以上,金庸亦趁機把大量股票轉售于品海,獲利以億元計。金庸一向自翔善於觀人,曾對筆者說,他只要與人談話幾分鐘,就知道這個人的人品如何? 能力如何?可以放在報社那一個崗位上﹗金庸親自扶持的繼任人,沒有按照金庸的部署行事,除了主管經營行政,也迅速的掌控了編輯部,金庸想做「太上皇」的美夢很快破碎了。1994年的農曆新年,我到《明報》董事長室,向金庸拜年,金庸剛辭去了名譽主席的職位,正在收拾辦公室內的東西,要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《明報》,一臉落寞無奈的神情。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金庸的這種無奈﹗然而,沒隔多久金庸就約我談創辦新報紙的鴻圖大計,想重出江湖,再起風雲。可惜不久金庸心臟病發,所有計劃告吹,不然,香港又是另一番風光了。
1995年7月18日下午,我按下港島山頂道一號豪華府第的門鈴,金庸在灑滿陽光的大廳和我說起了創辦《明報》的前塵往事。金庸用江浙口音的粵語說﹕「文人辦報,我大概是最後一位了,香港沒有了,大陸大概也沒有了。」語氣平淡中帶點無奈,眼神放空,陷入了沉思當中。
上一個世紀的報紙老闆,無不以戴上「文人辦報」這一冠冕而自豪,甚至看成是個人辦報成敗與否的最終評價。「文人辦報」是中文報業有別於西方報業的一個悠久傳統。清朝末年,西方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後盾,在中國辦起了報刊,宣傳基督教義之外還刊登天文地理聲光化學,兼有歐洲政聞國會議事,讓讀書人大開眼界,從此國人也知道了西方報人社會地位之崇高及報館對國家的貢獻。甲午戰敗後,舉國沸騰,康有為、梁啟超等公車上書,倡議廣設報館,振奮民心,於是書生以一枝健筆、一顆言論報國之心,重言教而輕牟利,成了「文人辦報」的詮釋。
金庸自稱是「文人辦報」,自也有「文人辦報」的局限,那就是只罵宰相,不罵皇帝。對國民党也好,對共產党也好,金庸的筆鋒,只會放在蔣經國和毛澤東身傍的人,是宰相誤國、宦官誤國,金庸也像歷朝歷代的士階層,絮絮不休的婉轉向領導人進諫,把希望寄托在領導人身上。
金庸是不是最後一位「文人辦報」,有待爭議;金庸經常批評讀書人辦報,不善經營,以致國人的民營報業,鮮有如英、美的大報,可以持續經營一百年、二百年。金庸也屢屢對筆者說,報業的理念要長存,報社要長期經營下去,非得「企業經營」不可。從金庸的理論和報業管理實踐來看,與其說金庸是「文人辦報」,倒不如說金庸是「儒商辦報」,更為貼切。金庸去世前的二十年社會活動,從接掌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到劍橋大學讀博士再到三度修改15部金庸小說,一一反映他晚年依然好學、執著,對世事難以放下的心情。張俊生所編的《鄉踪俠影》,紀錄了金庸以「大神」形象參加以金庸命名的各式社會活動,如「華山論劍大會」、「龍泉問劍」…大俠的連場路演,引來的毀譽不一。金庸從2002年至2006年三度全面修定小說,金庸小說專家、前《明報》督印人吳靄儀大表不滿,認為金庸企圖把昔日的遊戲文字變成金學研究,把小說改得太過政治正確,卻不好看了。吳靄儀認為金庸和其他文人一樣,血液中有親近權力中心的慾望,他以大俠的形象,長期在報社以低薪剝削員工福利… 平心而論,香港報社薪金偏低,是普遍現象,在處理薪酬問題上,金庸只是從大俠轉換到老闆、商人的角色而已。金庸辦報理念多次引起爭議,如金庸評論新聞自由時曾說,新聞自由是屬於老闆的,是報業老闆以此向外界爭取的自由;金庸又說,報紙是老闆的私器,不是社會的公器。金庸這些出格的言論,引來多個新聞專業團體的評擊。
金庸晚年潛心修佛,出殯時家屬派發的「金庸紀念冊」封面是金庸為潘耀明題寫的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」,如果這是金庸晚年的寫照,或許這就是金庸晚年最好的祝福了﹗
上世紀畢竟過去了,「文人辦報」的年代也過去了,金庸辦報寫社評的一枝筆,完成了歷史任務,留下了豐富的辦報經驗,供後人汲取養料,深信會有更多有文化承擔的儒商,迎難而上,為華文報業開闢新天地。
金庸的另一枝筆寫武俠小說,筆下的主角,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,挺身而出,拋頭顱、灑熱血,轟轟烈烈,寫出了全球華人知識份子心中的烏托邦。金庸雖然走了,他和梁羽生開創的這片江湖,後繼有人,精采不斷。